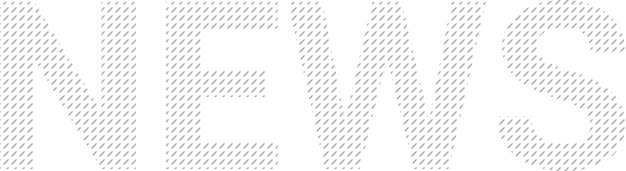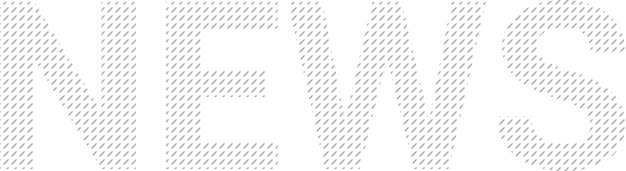清华美院白明教授
库艺术=库:无论水墨、油画还是陶瓷,您的作品是根植在“东方根性”上的当代转化,对于从传统中转化出来的作品,您觉得如何可以成为新的经典?
白明=白:从传统中转化出来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?这句话本身是不成立的。因为“如何转化”和“经典”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对传统转换的作品,并非都能成为经典,而是要学会转化,而且它还要经得起学术的考验和挑剔。只有它的影响力让人们产生共识以后,这件作品才可能成为经典。经典是交给未来的,但是转化一定是现在的。
库:水墨和陶瓷是中国独特文化和艺术媒介,您如何看待水墨的当代性转化问题?
白:东西方很难站在共同的文化认知上来看待水墨,当代水墨更多面对的是西方市场。中国凡是水墨玩的比较好的人,到了后来都跟“平面表达”没有多大关系,他更多迷恋材质的唯美性。很多人依赖这种美感给予的心理满足持续前行,而西方人如果不能有相同的审美,他就看不懂你所表达的内涵,所以一张薄薄宣纸上的水墨作品,在面对丰富立体并极具视觉刺激的当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中,其平面性处于劣势。但中国人对水墨创作过程的迷恋和满足,就像喝茶一样,能从中获得一种愉悦感。我们喜爱喝茶,就像西方人喜爱喝咖啡一样,更多是源于内心的一种依赖。
中国画家通过水墨的笔、水、纸之间的关系,获得内心的满足和愉悦感,这种愉悦是很私密的,是很难表白和言说的。在这种材料接触里,艺术家到底走到哪种自迷的状态,只有他自己知道,而人也只有这样,才能产生巨大的表达冲动。所以你因一样东西获得安慰,并由此进入了这样的状态,你就离开了这个时代,从而被它带入另一个空间。这种感觉让人迷恋,它不仅“私密性”有关,也类似有某种致幻的感觉。对待瓷土,我也是这种感觉,如果隔一段时间不接触它,就会有失落感。
面对瓷土,当我拿着青花颜料慢慢去染色,然后看坯体吸附料水的流畅、缠绕和渲染,在那一刻你就觉得心神舒畅,身体健康,这远比外在物质更能给人愉悦。因为纯粹的物质不会让人有这样的美感,这一点是陶瓷与水墨最基本的价值。至于在这个迷恋过程中,我能否创造一个新的形式,那是另一个问题。
中国人喜欢材质本身的美,只有经历过这种传承和文化记忆的人,在封闭性的个人艺术实践中才能体会到。没有这种体会的人,只能站在外部来进行主观的判断,就会像艺术史学家一样,往往把核心的东西敷衍掉。很多东西不要去问为什么,它可能就是一种“美感”,就像南方人喜欢吃米饭,北方人喜欢吃馒头,这是根植于各自不同的传统习惯和根子里的东西,它能让你获得真正深刻的满足。尽管艺术的形式是走向“未来”的,但通过艺术所表达的深刻感情肯定是往童年寻找经验和依赖,从而获得那种潜在的自我满足。它是一个“寻源”的过程,往“童年”也是往人类文明的早期共性里掘泉,这也是中国水墨被大家关注的核心心理需求。
库:您如何看待水墨未来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的可能性?
白:其实我不是很看好水墨会成为国际性的语言,就像我从没看好西方的某种艺术形式会永远成为国际性的话语一样。水墨是有瓶颈和门槛的,东西方对世界的认知不同,只有东方人会对水墨感兴趣,所以水墨作为载体在中国、日本、韩国获得发展,我觉得已经足够。水墨作为东方的艺术形式对西方的当代艺术家产生过一些影响,但不说明西方会普遍接受这种艺术,但水墨一定会成为中国人很依赖的一种表达方式,无论世界怎么变。大家不会因为水墨在未来很难进入国际主流而放弃它,中国人对水墨是源于心灵的需求,只要这种材质还在。每个个体艺术家的推进与尝试,都会慢慢产生力量,人性也是这样。
当人向着童年和过去追溯,也许以前很小的记忆会被你放大,这种放大其实是生命的需求,你需要在手里紧紧抓着一点东西,否则你后面的人生是空的。你“无意”抓住的,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东西,它对生命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,但你往往不知道它的存在,因为它根植在潜意识的深处。画家无意识几笔所表达的内涵,往往是最值得追问的。比如我非常欣赏通布利,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表达形式极其重要。我觉得水墨在未来的发展,一定会产生视觉上的巨大变化。水墨的当代性转化,不是从案头走向立体或放弃对毛笔的使用等外在形式,因为这只是一时对新的语言形式的引导,但不会成为主流。水墨转化的真正核心应是对中国整体文化的族群性思考,它最终一定会出现在极少数几个艺术家的身上,表现出这种破茧而出的成果。这一定是从内在形式里所产生的突破,在审美的深层结构里,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上,赋予一种更新、更本质的纸、墨、笔与人性和时代的独特关系。
库:与传统瓷器所表达的“精美”不同,您最近的瓷流露出一种“拙”或“缺”的状态,这是为什么?
白:我画油画,也画水墨,但我更主要表达的空间是瓷土。通过瓷土这种材料,我不断深入自己的观念和创作。瓷与陶不同,在全世界不同的文明里,我们都可以看到陶的使用,而瓷则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。我选择的是经过人为淘洗过的瓷泥,因为它的本质跟中国文明史里的独特性有关。中国人为什么能发明出这样精美且能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材料?对这个问题的思考,会引发你很多美好的想象,以及对材质的深刻理解。
我过去最喜欢磨练自己的技术,因为瓷需要很高技术来表达,它的分子越单纯,黏合性就越差,所以在使用过程中,任何外力的施加都会破坏它的应力,当应力被破坏,看似好好的一件作品随着干燥就会显出“伤害”。它是一个极单纯但又永远容易受伤的材料,很高贵、文雅,而又很脆弱,却很有尊严,所以在严格意义上,它真正具备了贵族文化品质。
我在年轻时,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来认知、控制和表达它的精美。但人就是很奇怪,当你的技艺和认知不断进步,你又会不满足于这样的“精美”和“完美”,希望通过人为的掌控做出更符合内心需要的东西。在早期作品《大成若缺》中,我对原本很完整或完美的作品施予一种破坏,使瓷原本作为“泥”的朴素语言得以凸显,并使其产生一种类似“浮雕”的感觉。当瓷脱离了精美的釉层,语言被还原到“材料”的本质,这传递出一种更为别样的感染力。顺着这个探索不断深入,我后来通过《太湖石》来探究空间与空间的关系,这不同于传统太湖石的“瘦漏透皱”。我的《太湖石》是表达“孔洞”与“孔洞”之间的美学关系,这是在人为控制下的,而非完全借助自然,我把它转变为另一种新的视觉关系。
库:面向“结果”的创作过程,逐渐让位于对“过程”本身的追问。您如何在自己的艺术中理解“过程”与“结果”?
白:当你观看我的作品时,看的更多的是“结果”,比如眼前这几十种不同的杯子形态。通过“形态”所看到的,包涵了前人总结的各种美学——自由的、有生命力的、精美的、理性的、表现主义的等等很多,但我们凡是把点落在了“结果”上,其实就很难突破了。“过程”中有很多东西容易被人忽略掉,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再去看的时候,会发现“过程”里原来蕴含着很多的可能和存在。比如在陶瓷烧制过程中的“开裂”或“断裂”,它在别人看来是有问题的,但我从中获得一种启示,那就是——如何通过这种“裂”的缺憾来表达我对“过程”的理解。
在我们以往的认知里,水是滋润泥土的,但我在拉坯的过程中,哪怕是多加一点水也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开裂;或你用细细的金属划过柔润的泥坯,你最初看不到一丝痕迹,因为这就像拿刀在水中过。但随着瓷坯慢慢的干燥,你所刻画的痕迹就会慢慢张裂显现。其实我们远远没有研究透材料本身的丰富性,你不要以为一张纸、一个瓷土,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已经被玩到了极限,其实很多人还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了解。瓷这个材料本身的脆弱和劣势,古人也注意到了,所以他们在制作过程中,通过趋利避害,在表现瓷的完美性上,古人做到了极致。而我现在想的是——如何不回避它本身的特性和缺点,让它本身成为我要表达的东西,回到“天真”。
很少有人用完整的实心瓷土做一件大型的作品,因为当你做一个大的东西时,会天然面对开裂等问题,那我如何完善开裂给我的启发,我如何通过别人认为有问题的“断裂”来表达我对过程的理解。“断裂”其实是自然给予的启示,通过这一点我后来做了很多作品,从而传递的一个观念是——怎么看待这个材料呈现的结果。
经过几年这样的实践,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,更多希望的是瓷土在不受保护的情况下,得到一个自然的呈现。比如我在创作过程中,不再用塑料袋或布去包住瓷土,不再注重让它的水分得到同步干燥的呈现。当你对瓷泥施压的时候,它们有的裂成一条缝,有的裂透,有的完全脱离,有的却是多条的浅裂纹……这种断裂在视觉里不断给予你启迪与思考,你就会产生与以往不同对自己却显出重要的深刻的认知来。陶瓷要经过火烧,我把它们分开在不同的窑火里确认,让它的力量感、与火接触的点和气氛都不一样,最后再把它们组合到一起。你会发现原本一体同胞的泥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,它的“裂”决定了它们的走向和容颜,最后又组合成一个新的“自己”。透过这些,我也靠近了自己。
库:您的艺术已经是对于“瓷”这种材质的全新认识,它的指向不再是精美的工艺,而是艺术家的独特观念和个人价值的投射。
白:我已不再把瓷的“精美”作为表达的核心,我做的是对“材料本身”的还原,由此呈现它不被技术所覆盖和规范的真实表情和性格。
我最近经常思考的是——当我成为“瓷泥”本身,当我不再控制它,让它在自然的状态下,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生命感、形态或光影?我最近在葡萄牙的展览,他们的策展人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叠加的关系》,文章的主题用的是我作品的名称。在这件作品中,我将几个泥片卷在一起进行叠加。我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件作品,破解我过去所依赖的经验,以及对传统艺术中“精致”审美的迷恋。对于传统,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,无论是白釉、青釉,还是青花或彩瓷,其颜色足以让我们移不动脚步,但它们是在过去的“完整程度”里呈现的。叠加的关系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呈现。
我在创作中,选择的是经过人为淘洗、处理过的瓷泥,这种瓷的贡献是我们的先贤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。当你在一个世界的范围里去理解,就会产生一种自豪感。芸芸众生,为什么是中国人发明出了这种提升人们生活和生命质量的美丽物质?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,会让你产生很多想象,而这种想象恰恰是艺术家极为迷恋的。我不需要得到正确的解答,但是在这种想象中,我会产生更多对材质的新的理解。
摆脱以往的惯性经验,学着逆向思考,让所有感知保持在最初与泥土接触时的状态,这是我创作的源头。在《延展与断裂》中,我用泥做成一个类似波浪纹的形式,这其实就是延展,但它在伸缩时会断裂。其实“延展与断裂”是文化的关系,也是历史的关系,也是时间的关系,它与我们的族性有关。
我近来做了一件巨大的“城墙”作品,结果半年以后,在烧制的过程中炸裂,但炸开的作品碎片所表达出的光影和纯粹性,以及力量感给我极大的震撼,它们像极了远古的人类打制石器,具有强烈的意志。我想,原始人可能是看到过岩石崩裂所产生的力量感,进而学会运用这种力量,于是他们根据岩层结构的走向来打制他们的工具。我没想到一块完整的泥在烧制时会因气孔炸裂,也能形成这种形态,这是否是热能对人类显现的对自然物质认知的暗示,是否是通向“自然”的途径?艺术的创造大多受到自然的启示,只不过很多人找不到“引发”创造的原点,创造就成了抽象。
抽象艺术家巧妙地隐藏了“引发”的过程,只让观众看到他从真实的世界、经验、情感、技术里表达的东西,他把中间所有的引发过程都很好地隐藏掉,最后只呈现为一个抽象的画面,其实这不是抽象。因为对于一个真诚的艺术家而言,都是真实的“具象艺术”。我通过另一个角度,看到“过程”给人的视觉。我将所有炸裂的碎块进行编号,然后烧制成瓷,取名为《熵》。就像人的生命力,也是“热”的力量。
每个人在创作过程中,不要依着习惯和多年的技术、审美、经验去走。
库:通过这一系列极为个人的思考和观察,事实上“瓷”在您的手上已经转换成为了一种当代艺术的“媒介”,这背后的思考极为个人却又具有普遍性,这正是一种传统的当代转化的范例。
白:容器其实是最抽象的存在形态,它具有极强的当代性。无论从哲学观还是美学意义上,人们赋予容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,比如一个圆瓶,它给人圆融、和谐、可爱、饱满的感觉;而一个长瓶,则给人向上、舒展、修长的感觉。它没有语言,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东西,让人产生由视觉带来的丰富联想。在一条线的约束之中,让人联想到很多自然里拥有的东西。当一条圆线受到破坏时,你就觉得“缺”,艺术家就利用这一种“缺”来表达情绪和变化,这就是线条的情感。中国的容器带来了抽象的思维。
(图、文:陶瓷系教授白明提供)